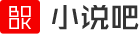百味孤独的羔羊小说
风从粗糙的木栅栏中间穿过,将一把上锈的铁锁刮得吹起尖细的口哨。一双眼睛正透过铁锁向栅栏里望,栅栏为羊群阔成一个方框。一大早,热乎乎的羊群被韩老汉撵到就近的西山坡上去觅食,现在方框里只有一只老羊躲在角落里,这只眼睛扫过一片空阔后,激动地落在老羊的身上。她不安分起来了,将手竖成一扇刀片从栅栏缝里伸进去,突然,她惊喜地扭动起身子,她发现她的短小手指竟然摸到了老羊灰色的卷毛,声音在她的喉咙里激烈地翻滚起来,她压低了嗓子唤:“老姆那,老姆那……”
一股风夹着雪嗖地伸进栅栏里,将老姆那瘦削的身子骨又搜刮了一圈,老姆那朝着她抖动了几下卷毛,扇了扇修长的睫毛,两只眼睛立时注了水一样湿润起来。老姆那努力地朝着她晃动起身子,它下身沾了干瘪的粪蛋,有它自己的也有别人的,缠在打绺的赖毛间像串着珠子的门帘,到了冬天,珠子上又裹了一层冰,随着动作在腿间叮当作响,它起了几起还是放弃了,一口粗重的热气在嘴里叹出来,整个身子就塑成了一尊僵在雪地里的雕塑。
她不停地唤着老羊的名字,唤声被突然从屋子里灌出的韩老太的叫喊声切断:“花花,哪里去了,吃早饭!”花花浑身打了一个哆嗦,她迅速将手从栅栏缝里抽出来,像一只受惊的小鼹鼠转身朝院子里钻,雪吱吱呀呀绊住她的脚,她突然想起什么,飞奔回栅栏边,对着老羊轻嘘:“等着我,老姆那!等着我!”说完,花花摆着一副脸朝后身向前的姿势又向着门口飞奔去了。
韩老太就要迎到大门口,花花像一只箭射过去,途中顺手抓了几把雪涂在裤子和鞋面上,一副顽劣的样子。韩老太的阔身子像一座钟摆镶在门框里,看到花花,她满脸的褶子上了发条迅速拉紧,“又玩儿雪,小心狼叼了你去!”她郭起厚腰板,将花花从屁股到脚跟拍打一遍,钟摆就笨拙地围着花花摇摆起来。韩老太扎着火红的围裙像肚子里包裹的一团火,直烧到雪地里,她的那双 低垂得像一对棉线锤敲打着花花的头顶,花花一伸手抓了满把,嘴唇就要凑上去窝动起来,韩老太的笑从脸上抻开了,“早上还有一杯奶喝!”韩老太伸直了腰板,对着花花挤了挤眼睛,“老姆那还能挤出一杯奶!”没等花花高兴地蹦跳起来,花花已经变成一只鸡仔被韩老太擒到院子里。
院子极为阔绰,像一大片麦田,红砖墙四周围了无数捆玉米杆,像站在雪地里的侍卫。十八连的院落都是这样子阔大,黑龙江的冬也冷得实诚,整片院子冻僵了,雪盖了一片,韩老汉像一颗黑色的羊粪蛋儿卷缩在井边擦擦擦磨着刀子,整个连队没人在寒冬腊月冰冻的院子里磨刀,韩老汉是独一份,一盆热水,一块磨刀石,一块黑抹布,刀就磨起来了。
雪白的刀子被晨光镶了一层铜红,仿佛刀尖上滴出血来,像冰水一般榨人的骨头。暗红色的布条缠了半截刀把,又甩出半截红尾巴坠在刀的屁股后面,随着韩老汉的动作舞动。花花打了个寒噤立在雪地里,“奶奶,爷爷,不冷吗?”她想打断韩老汉的动作,她对这种擦擦擦的声音恐惧,让她想起无数只被这声音杀死的羊,她立时把身子缩成一个棉球畏在韩老太的大腿根儿,韩老太几步将这个棉球护进了屋子里。
韩老汉不抬头,卖力地耷着他的黑脸,似乎将全身的力气运在手指上,好将整颗脑袋憋成黑青的石头,叫人见了心里生紧。韩老太扭出屋,站在韩老汉跟前双手搓着火红的围裙,像揉搓着一把炽热的火球。她对着韩老汉的棉脑袋颤颤地叫喊:“吃饭,老头子。”韩老汉闻听更用力地将脑袋点成捣蒜的姿态,擦擦擦几乎将刀尖活生生扎进磨石里。韩老太蹲下身子来,“今儿就杀老姆那,缓缓也成?”韩老汉突然爆炸,“就今天,杀!”眼前的韩老太被炸瘫在雪地上,花花将扒着的门缝哐当紧闭,顺着门溜到地上一小撮,她紧紧咽了几口唾沫,心里惊呼:“杀,杀,老姆那!”
屋外的韩老太从雪地里爬起来,拍打着屁股上的雪,嘶嚎:“你个没血性的!没血性!”她咬着嘴唇摇头晃脑地进了屋子,不管不顾地和花花吃起早饭。红豆包像女人的 一样拥挤在簸箩里,花花爱吃这,她说像是在裹奶水。韩老太就常给花花蒸些红豆包,特意在圆白的豆包顶搓一个圆润的 。今天,花花坐在桌子前愣怔着这群 ,韩老太递过来一个,花花接在手里又放进簸箩,她只喝了一杯奶,喝完,将杯子举得底朝天,用尽全力将舌头伸长,像一只壁虎吸着杯壁上的奶渍:“老姆那的奶真好喝!”杯子落在桌子上,花花的眼里喷涌出奶渍般的泪。
韩老太把鼻子簇成一个肉疙瘩,在半空摆着干枯的手掌,将花花搂在怀里。她的身子抖得软稀稀的,像老姆那晃荡的被羊羔抽干的 。她又将花花往紧里搂了搂,狠狠将花花的头埋在自己胸前,几乎夹在她那两拖倒吊的干瘪的布袋里发着抖。老姆那的奶水不丰厚的时候,花花就在奶奶的干布袋里拱得昏天黑地,奶奶的的那片天地里总是干涸得充满裂缝,龟裂般的 暴着白皮,纵使花花将嘴唇裹得脱了皮般生疼,干旱也是难解的。
两个人正抱得紧,韩老汉进了屋子,手上还沾着磨刀石的灰青色未洗,就闷头摸起红豆包塞的满嘴都是。花花嘟囔着尿尿,从韩老太的怀里挣脱出了屋子。院子墙角一个铁罐子,那是花花夜里用的,她浑身打个激灵将一注尿液装进罐子里,热乎乎的尿骚味和羊膻味就凝结成一朵一朵的怪味儿豆。花花一侧头,亮闪闪的刀子趴在雪地上眨着狡黠的眼睛,花花的愤恨就涨满了胸脯。
她蹑手蹑脚像一只螳螂挪到水井边,将刀子掩在花褂子下面出了院子,她拼命地向家后的荒坡上跑,仿佛爷会变成一个屠夫在身后疯狂地追赶上来,又似乎这把刀子要杀的不是老姆那,而是花花自己。她甩起两撇小辫子像上劲儿的马鞭,跑了几步便成了爬,雪厚得把她的膝盖吞没了,她没法子,撅着屁股把一条腿从雪窝里 ,迈一步塞进雪里,再拔另一条腿,一路摇摇晃晃像个费力的跛子。她每走一步都在嘴里念一遍:“老姆那,老姆那,你等着我。”声音越嚼越小,气越喘越粗,嚼成一撮白粘沫贴在嘴角,像是吸剩的奶渣。不一会儿花花的脑袋向着天空竖起一柱柱热气,像蒸熟了一锅发面馒头。
荒坡向另一座矮山头绵延,雪又把它们和远处的群山连在一起。花花朝着荒坡上的荒草林里爬,雪越向深处越厚的扎实,淹没了她的大腿根,她紧握着刀子不松手,另一只小手扒在雪上,手被冻僵了,像一根丢弃的熟烂的萝卜头。雪沾了满怀,又钻进裤筒和红条绒布的棉鞋里,湿潮潮地从脚心向身体四处泛着透心凉,连她的下巴也没有放过,被雪和风搓的通红。花花爬几步,拼命地甩甩麻木的手掌,她突然张了大嘴要哭个痛快,脑袋一抬,眼缝一撩,窝在荒坡里的那颗小树苗子钻进视线里,她立时把嘴闭上,紧咬嘴唇,将整个身子匍匐在雪地上快速地爬行,像一条受惊的草蛇。
树苗子扎在雪窝里足有两个花花那么高。一见了树苗,花花练起了狗刨,她赤着手扒树苗根下的雪,直到掏了一个雪洞,露出荒草地皮,地皮拱出一个土包,已经被雪压的实诚,她用刀子剜。黑龙江的冷像韩老汉的那张黑脸一般强势,别想有一丝一毫逃出被冻结的命运。刀子被韩老汉磨得锋快,冻土也畏惧了,被削的粉身碎骨。花花一边剜着土包,一边探头朝荒坡下的屋子瞧,出来的时间长了,她生怕爷奶会四处寻她,逮她一个现形,先前埋在土包里的秘密就会被掀个底朝天。她继续将刀子甩的像鼓动的风车,手掌再不麻木了,像撒了辣椒面火烧火燎的。她顾不得了,将土包削成一片片的土豆皮,只听咔嚓,金属撞击的声音终于跳跃出来,花花也跟着蹦了个高,她用刀子将一个铁盒子从土里剜出来,盒子锈迹斑斑,是爷爷丢弃的破工具盒子,一打开,一堆羊的后腿上的髌骨匍匐在里面,密密匝匝,见了天日,都张着嘴向着花花呻吟。
在黑龙江人们把这骨头唤作“嘎拉哈”,四个成一组,每块儿骨头四个面儿,较宽的两个面一个叫“坑儿”、一个叫“肚儿”,两个侧面一个叫“砧儿”、一个叫“驴儿”。再用旧布头儿缝制一个小方口袋儿,装上粮食。玩时,把小口袋抛到空中,迅速把炕上的“嘎拉哈”改变方向,然后在口袋掉下来时及时接在手中,如此往复,直到炕上所有的“嘎拉哈”都改变过四个方向为止。连队里的孩子没什么玩具可玩,三两一伙,四五一堆,欻嘎拉哈,小到七八岁懂了事的,大到二十几岁未出嫁的女孩子,都喜好拿这取乐子。花花见不得这,也从不玩这,每次韩老汉将剔下的嘎拉哈打磨得干干净净丢给花花玩耍,花花都偷偷藏进这个铁盒子里,埋进这棵小树下。
她有种怕,每次韩老汉在院子里杀羊的时候,羊救命的叫喊声就像这把刀子一样朝着她杀过来,她最怕的是将来有一天吊在院子粗绳子上的会是老姆那,她曾背地里问过韩老太,韩老太摇着脑袋说:“羊和人一样,都会老,都会死。”从那天起,这个铁盒子里装进了韩老汉杀过的每一只羊,今天,花花终于得逞了,可以让这罪魁祸首的刀子彻底消失,老姆那就可以长命百岁了。
花花沾沾自喜地匆匆把刀子装进铁盒子里,盖了土,又把大堆的雪推过去,用两只手在雪堆上结实的拍了两下。她幸福极了,像一只袋鼠蹦跳着回了家。栅栏里,老姆那正焦急地一圈一圈地蹒跚,它嗅到了浓烈的血腥味儿,两只眼睛鼓胀的像一对红灯笼。花花跑过去,把整张嘴伸进栅栏里,对着老姆那的灯笼眼上气不接下气:“老姆那,没事了,你等着我!”说完,她老鼠一般钻进院子里。
屋子里热闹的很,一片惊天动地的嘈杂声,似乎是锅碗之类的锐物被摔到地上,韩老太尖锐的吼声被放大得变了腔,只听见丝丝裂裂哑二胡般的拉扯声:“毒心的老东西,老姆那晚几天死会折了你的阳寿?!”话没说完,叮当轰隆声就炸成一片,夹杂在韩老太的吼声里,“花花,花花咋离得开老姆那,眼睁睁地看着它死!”韩老汉除了大动作地摔东西,会把鼻孔鼓得水牛鼻子一般,粗气就从这阔大的鼻孔里浓烟滚滚滚地窜出来,像屋顶乍起的两个粗烟筒。这样的声响花花听得习惯了,从她能听到声音的时刻起,爷爷奶奶酿造的这般争吵的声音就像老姆那挤出的奶一样苍白了。
花花只是觉得这天更冷了,她满头的汗已经泄了,经风一吹,起了一层鸡皮豆,她悄悄地朝着屋门挪过去,身子轻小的如一只灰皮老鼠,门没打开,韩老汉一声声嘶力竭的吼叫硬生生把门劈开了:“杀,杀,杀,一刀就他妈什么都了结了!”他像一只发疯的饿狼,蹿到院子的水井边,陀螺一样旋转着寻找他的刀子。花花趁机一溜烟从门缝里挤进去。
屋子里一片狼藉,像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。花花呆在门口,背紧撮在木门上,她的心遇了冷冻般缩成一个球,她六岁了,六年里爷奶从未闹过这样凶,花花不知所措,两只手紧抠着门框,从喉咙里憋出怯怯的声音“奶奶,奶奶……”韩老太从地上爬起来,用她粗糙的耷眼皮遮住浑浊的眼睛,一把把花花掠到怀里,哭声就劈头盖脸地四溢了。
院子里的水盆被踢飞了,叮叮当当脆响一片,磨石被抛到半空,哐当砸在水井上,仿佛大地立时被震裂了大洞。韩老汉一番大动干戈后又吼开了,“刀子!他妈的刀子呢?!”院子空旷,像安了扩音器,吼声翻滚着扎进屋里,将屋子里的两个人惊的一哆嗦,像两只雏鸡更为紧密地挤在一起。
韩老汉真的气疯了,那把刀子随了他几十年,和他的亲兄弟一样,干起活来利落风快。他将栅栏边的玉米秸一捆一捆地搬倒,溜着栅栏一步一步地堆在雪地上寻找,院子立时变得人仰马翻。他突然对水井动了念头,伸腿在水井上踹了几脚,然后侧着耳朵贴在水井头上听,没有刀子清脆的落井声。他鼓起了牛眼,扎起他的大骨节手,把井头上冻结的螺丝扭得吱吱呀呀呻吟,螺丝一落地,井头咔嚓卸下来了,韩老汉伸着眼珠子向里窥探,“他妈的刀子?”
屋子里的两个人已经来到院子里,不做声,站在韩老汉身后看着魔鬼般的他在院子里发着狂。韩老太从地上拾起水盆子朝着韩老汉砸过去,“疯了,你个死老头子,不让人活了!”盆子刚好从韩老汉的头皮擦过去,把韩老汉砸醒了,他把目光嗖地投到两个人的身上,像两盏小鬼子的探照灯悠来晃去地在韩老太和花花的脸上扫射,花花揪紧韩老太的红围裙,朝着她屁股后头钻。韩老汉一下子明白了,刀子般的眼神追过去,“花花,刀子!”
花花被逼的一个趔趄堆在雪地上,她惧怕地张开大嘴哭号,她觉得爷已经不是爷,而是个凶悍的侩子手。韩老汉闪过去一手将花花拎起来,像提留一只瘦鸡仔,“花花,刀子!”花花张着嘴哭喊着摇脑袋,韩老汉的大手掌结实地糊到花花的屁股上,“叫你偷,你偷,没爹没妈的种就会偷!”花花突然京剧变脸一般止住哭,她紧咬嘴唇,狠瞪着韩老汉的黑脸,“不知道!就是不知道!”韩老汉和花花像一只虎和狮子对峙,花花将眼睛瞪得石头般坚硬,接住韩老汉的刀子眼,她用眼神告诉韩老汉“我没偷!”
韩老汉的怒气在脸上杀了一片青黑,眉头上了锁,巴掌又糊过来了,落在花花的脸上,立时鼓起了五个手指印,“叫你倔,叫你偷!叫你撒谎!”花花把脸一扬,结实地迎住这五根手指头,她不做声,她歪着头把牙齿咬的咯吧作响,她把一对眼睛瞪得目空一切,将眼前的韩老汉揉搓成羊身上一只黑色的跳蚤。韩老太几乎惊呆地瞧着眼前的花花,她突然醉酒醒悟般把硬板身子拱过来,将韩老汉撞到一边,“花花,我的花花。”韩老太将花花搂在怀里进了屋子。
共 9710 字 2 页 转到页 【编者按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被吸引住了,我在想孤独的羔羊到底是指什么呢?怀着好奇心看下去,我被一个孤女和一只老羊的哺乳之情感动不已,有时感情超越了种类。老羊最后死在狼口,巧妙收尾。善良是人的天性,看似凶残狠毒的韩老汉也有一颗柔软细腻的心。很平凡朴质的小故事,但是意蕴深远,看得出作者是一个善良实在的人。文章首尾连贯,段落连接有序,语言含蓄,耐人寻味。一篇好文,倾情推荐。遥握!【:梁心】
1楼文友: 06:48:26 感谢赐稿,期待你的更多精彩。
灯盏花制剂好用吗
灯盏花制剂怎么样
灯盏花产业怎么样
宝宝厌食怎么办怎样才能治宝宝感冒流感
小便黄赤失禁是什么原因
- 06月21日历史大瑞士山地犬体味程度该犬体味较轻位置
- 06月21日历史大白熊犬刚打完第二针疫苗可以洗澡吗位置
- 06月21日历史大白熊犬会护主吗训练大白熊犬护主的方法位置
- 06月21日历史大斑点狗多少钱一只成年斑点狗主要看价值位置
- 06月21日历史大山雀的饲养方法位置
- 06月21日历史大学生网购宠物狗四天奄奄一息疑似购买星期位置
- 06月21日历史大狗能吃生鸡蛋吗狗狗应该怎样吃鸡蛋位置
- 06月20日历史吃番茄的狗狗真的不怕酸啊位置
- 06月20日历史合格成员位置
- 06月20日历史叶形鱼怎么养适宜温度位置
- 06月20日历史史毕诺犬怎么养喂食量应当固定位置
- 06月20日历史吃水果对藏獒的身体有好处吗位置